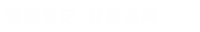与上面一段写“快”,写“受命之亟”相对照,接下来一段,史公写“慢”,写“一统之难” 。
昔虞夏之兴,积善累功数十年,德洽百姓,摄行政事,考之于天,然后在位 。汤武之王,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;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,犹以为未可,其后乃放弑 。秦起襄公,章于文、缪、献、孝,之后稍以蚕食六国,百有余载,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。以德若彼,用力如此,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。
“虞夏之兴”一句,是讲舜、禹个人,受禅而“在位”,靠的是善功德行,得到了“百姓”的认可和“天”的核准 。虞夏尚矣,难以细节论,以下是平行的两条线,分别讲“汤武之王”和秦并天下的过程 。“汤武之王”不单是商汤和周武的个人为王,同时也是商和周分别以诸侯国之一,寖假而成为天下之上国,成为天下的“为王之国” 。不妨比照修昔底德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讲的“雅典帝国”和“斯巴达帝国”,那是分别以雅典城、斯巴达城为首的城邦联盟,为首即为帝,雅典、斯巴达是“为帝之国”,故联盟称“帝国” 。在方国林立的世界,这样的格局很自然 。希腊世界和华夏世界的一个不同则是雅典帝国、斯巴达帝国没有商汤、周武这样的个人为王 。秦并天下,秦帝国却不能与雅典帝国比拟了,那是灭掉了所有的诸侯国,纯然是、全然是以一个人为帝的帝国 。
汤武之王,各自经历过从他们的祖先契、后稷开始的“十余世”长期而连续的过程 。秦并天下,也经历过从襄公始封,中经“文、缪、献、孝”,至始皇始完成大业,长期而连续的过程,即使从孝公算起,也已“百有余载” 。过程都是缓慢,都是艰苦,不同在于,商、周之王是“以德”,秦并天下是“用力” 。然而史公又要强调不同中之同:“以德若彼,用力如此,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。”史公区分周、秦为“两种大一统”,两种性质不同的大一统,不同而仍有一同:难,“若斯之难也” 。
【司马迁论刘邦得天下:岂非天哉,岂非天哉】司马贞《索隐》解释“以德若彼”:“即契、后稷及秦襄公、文公、穆公也”;解释“用力如此”:“谓汤、武及始皇” 。换言之,商、周、秦,祖先都是“以德”,而后来完成“一统”的,都是“用力”;前人积德作准备,后人用力搏成功 。但这是司马贞他自己的意思,用来解释司马迁的意思,是完全理解错了 。
《六国年表》前言:“秦襄公始封为诸侯,作西畤用事上帝,僭端见矣 。”天子祭天地,诸侯祭域内山川,襄公却以诸侯行天子礼,太史公既说他“僭端见矣”,怎么还会许他“以德”呢?“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,君子惧焉”,话是说得很重的 。襄公之僭,尚属端倪,“章于文、缪、献、孝”,历经后来诸公,就越来越彰明昭著了:“文公踰陇,攘夷狄,尊陈宝,营岐雍之间,而穆公修政,东竟至河,则与齐桓、晋文中国侯伯侔矣”,“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”,“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” 。这些难道不是“用力”,倒是“以德”吗?司马贞只顾索隐,连这么明白的话都视而不见!
也许因为汤武也动刀兵,汤放桀,武伐纣,司马贞故谓汤武为“用力” 。史公此处未言汤放桀,言武伐纣足可代表:“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,犹以为未可,其后乃放弑”,一句三折,但语意很清楚 。八百诸侯,不期而会,一折;伐纣如囊中取物,“犹以为未可”,二折,节制和慎重,明显德意;“其后乃放弑”,三折,以德帅力,“用力”只须轻轻一拨 。此而不谓“以德”,而谓“用力”,岂非“用力”求一统很容易?史公竟是在自相矛盾了?
上一段讲“受命之亟”,这一段讲“一统之难” 。“一统之难”是商、周、秦的情况,“受命亟”而能稳定下来,倒是“一统之易”了,这是汉家的情况 。周以德,秦用力,此乃周、秦之异;周一统难,秦一统也难,此则周、秦之同 。秦用力,汉也用力,这是秦、汉之同;秦一统难,汉一统则易,这是秦、汉之异 。同为用力,而一统有难易,原因何在?下面一段(也是最后一段)就回答这个问题 。
- 有些新闻著作也称之为什么 有些新闻论著也称为威尼斯什么
- qq空间评论装扮怎么取消 qq空间装扮代码怎么用
- 五毛的官方称呼是“网络评论员” 五毛是什么意思
- 杀了刘邦项羽就能得天下?然也!匹夫之勇毕竟成就不了帝王之姿
- 刘邦为什么能得这么多能人相助?牢记这24个字你也可以
- 刘邦项羽两句不同的话成就了两种不一样的人生
- 孩子买回来个金毛不想养了
- 宣平侯张敖是谁?刘邦为何要捉拿女婿入狱
- 揭:昭示刘邦将夺取天下的神秘预言
- 历史上最悲剧的太上皇刘老汉被儿子刘邦气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