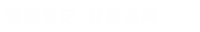它们的羽毛多么好看啊 , 乌黑乌黑 , 和白色的喙、黄色的脚配比得那么和谐 。它们在天空中飞翔的时候 , 姿态是那样优美 。我一直找不到词来形容、修饰 。直到上初中学到高尔基的《海燕》这一课 , 我才恍然大悟:对啊 , 可不就是“一道黑色的闪电”!我曾用稚嫩的笔这样写道:“它们一振翅 , 在天空中划过一道黑色的闪电 , 一敛翅掠入林中 , 又像倏然消逝的一缕夜色 。”
两只八哥的鸣声很特别(雄八哥高亢一点 , 雌八哥略为婉转一点):
“八个九~八个九”(“个”音很轻 , 一带而过 , “九”最重 , 音同“就”)

文章插图
一年四季 , 它们以或远或近的鸣声见证、宣告自己的存在 。后来我来到县城、都市 , 见到过人们囚在笼子里的宠物八哥 , 也在城郊的山林里见过野生八哥 , 但它们的鸣声都是单音节的 , 类似于啄木鸟或喜鹊的“喳—喳”或“嘎—嘎” 。夏天 , 是鸟叫虫鸣的盛季 。蚕永远是在知了知了地聒噪 , 油葫芦的声音悠长而拖曳着一些尾音 , 纺织娘在傍晚叫起来 , 像开了一支高音喇叭 。但我总能从无数重叠着的虫鸣鸟叫中辨别出这两只八哥的鸣声 , 雄八哥的高亢 , 雌八哥的婉转 , 它们或远或近或高亢或婉转的鸣声像是穿透岁月而来 , 来到村庄 , 这给了童年和少年的我多少欢乐与慰藉 。
然而一直让我纳闷不解的是 , 两只八哥为什么没有繁衍后代 。我查过《十万个为什么》:八哥一年孵巢一次 , 一次一般孵化两枚蛋 。八、九年时间 , 也该有十六、七只小八哥 , 小八哥还能生小小八哥 。照理 , 小八哥们必定继承了这两只八哥的基因 。当一群八哥“八个九~~八个九”地鸣叫起来 , 场面该是多么壮观 。然而一年又一年 , 我所见到的还是这两只八哥 。它们或许已经生下了小八哥 , 移居去了别的村庄和树林?但是我在四周的邻村的屋顶和树林见到过八哥 , 它们的鸣声都是单音节的“喳—喳”或“嘎—嘎” , 单调而暗哑 , 没有一个发出“八个九~~八个九”的鸣声 , 这使我坚定地认为它们必定不是这两只八哥的后代 。
或者 , 对这两只八哥而言 , 我们这座村庄的生存环境太过险恶 , 缺乏小八哥成长所需要的宽容和呵护 , 它们只好过起了现在所谓的“丁克”家庭的生活?
这个疑惑我曾经问过母亲 。母亲愣怔了半天 , 最后忍俊不禁地笑了 。她大概对这两只八哥是否具有这样的生存智慧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。
王小波有一篇散文名作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 。我以为 , 那是一只“虚拟”的猪 , 于荒诞中凸显“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”的象征意义 。而我的这两只八哥 , 完全是写实的 。我自然不会贬低它们 , 也丝毫没有刻意美化、拔高他们 。母亲曾以两只八哥为例对我进行人生启蒙:“做人要精一点 , 像那两只八哥 。一年过了一年 , 还在那儿飞、吃食 。”我至今学不会“精” , 但我喜欢这两只八哥的“精” 。否则 , 它们的鸣声就不会陪伴我的童年、少年那么多年 。有时候我想:假如人们将所能想到的卑劣手段使出来 , 下毒、拉网、砍掉那棵法梧树以及周边山林、毁坏它们的栖息地......它们的生存智慧还能抵挡那命定的厄运和劫难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