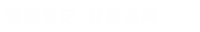作者:王音洁
如果拍一部反战为主旨的影片,但并不正面去谈战争,对于战争的伤痛是以外围边界的事件来轻轻触及,但绝不亲手揭开,那么我们还能不能感觉到痛?如果能,会有多痛?

文章插图

文章插图
图片来源/吉勒·利波维茨基的《轻文明》 一书封面

文章插图
《大象席地而坐》
把沉重轻说 是个问题
这是我看完以中国母亲寻找失联的养女——日本遗孤为故事的《又见奈良》后想到的问题 。这问题萦绕着我这么个闲人,无聊之际,还重看了一遍《清凉寺的钟声》,一部由谢晋导演拍摄于1991年,讲述日本遗孤在中国北方农村艰难长大,成年后以僧人身份访问日本,与生母相遇告别的故事 。它或可作为《又见奈良》的补余,供人们脑补影片没有展现的生活:一个日本孩子怎样在异国被收养长大/一对中国父母怎样养育他们收养的日本孩子 。另有一部同样展现这个过程的中日合拍电视剧《大地之子》(1995年),当年也一样轰动两国,成为一时热题 。这两部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影视剧,都把时间跨度从1945年日本战败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,非常完整地展现日本遗孤在中国土地上是怎样一年一年,随新中国这个大时代长大成人的 。那些个细碎重复的生活,喂养下去的一口又一口,一个婴儿变成了老人……
《又见奈良》隐去了这些东西,它直接从养母只身来到日本奈良找女儿拍起 。关于整个故事最要紧的历史背景,在开篇几分钟后,导演快速插入一段动画,形似弹幕,简单交代,再全力转入日本寻亲故事,再无镜头涉及过去的生活 。这是导演鹏飞特意选择的风格,他从上一部电影《米花之味》开始,就选定了这种轻喜剧冷幽默的风格,把沉重轻说,让观众保持观影的愉悦感,他做到了 。
《米花之味》针对云南傣乡留守儿童,《又见奈良》则围绕日本战后遗孤,背景设定都是非常沉重的现实话题,也是一层深厚的文本基础,帮小成本影片撑起某一种坚实维度 。但是厚实的历史和现实文本并不是现代可以随意套进去的一只手套,想穿就穿,想脱就脱 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,它能托着当代的创作者浮游翩跹,也能顷刻吞噬掉这叶轻舟,使我们显露出可笑的模仿姿态和力有不逮带来的言不由衷 。怎样用电影语言,来讲一个大历史议题里无数分叉下的小故事,这个课题并不新鲜,有无数中外前辈做出过很好的示范 。但怎样运用当代的媒介意识,来讲一个夹带着深厚历史文本与现实意义的小故事,这对于年轻导演鹏飞来说,应该是个问题了 。
我们已经起不了悲剧的范儿
豆瓣上有影评将该片命名为“轻影像”,取自法国哲学家吉勒·利波维茨基的《轻文明》一书 。书中谈道,“‘轻’逐渐支配起我们的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,它侵入我们的习惯,重塑我们的想象 。它在物品、身体、运动、饮食、建筑、设计等无数领域内成为一种价值、理想,和迫切的需要 。”在这个超文本链接的媒介时代,对于“轻”的多形态崇拜渗透进一切 。基于这样的定义,影评人将鹏飞采取轻松俏皮基调讲一个悲伤故事的电影,归之为“轻影像” 。虽然缺乏更多清晰的阐释,但这个命名似乎有那么几分道理,至少它提示我们一点,这种用轻松愉悦调性来表达现实或历史话题的美学风格,的确是眼下的一种“显学” 。
高科技的发展、新能源变革、互联网、新媒体、纳米技术……物质世界的一场巨大变革,使技术与市场更倾向于“轻”的逻辑而非“重” 。“轻”的规则不再是个人的事,而成为全球经济文化的运作模式,“轻”的逻辑不再是经济现实中的他者,而是经济现实的核心 。人们厌弃沉重的一切,只想以轻盈之姿流动之态重启文明——正像尼采所说,“美好之物是轻盈的,一切的神圣皆以灵巧之足奔跑” 。“不想沉重地说沉重的故事”,这大概算是“轻文明”时代之典型症候 。
的确,催生凝结着文明高光的悲剧意识的一切条件都烟消云散;召唤它重现的一切语境,都不再明显存在 。乔治·斯坦纳在《悲剧之死》里认为,古希腊戏剧在神话、符号、仪式参考的语境基础上诞生,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仍能够有想象力地遵循之 。此后慢慢地,给悲剧提供信仰和准则的古老意识,以及在共识中判断和识别的习惯就不再普遍存在了 。如果有幸具有极高的天分,比如易卜生这样,可以为他的戏剧创造一个富有思想意义的有效神话,他能够设计令人震惊的符号和象征、相应的文体和剧场手段,同时又彰显某种特定生活观念的象征性行动,再创生活观念,那么悲剧意识会再次到来 。而斯坦纳此处指的悲剧,是公元前五世纪就上演于雅典的“高悲剧”(high tragedy),或者称为“纯粹悲剧”,即讲述那些“不能通过理性改革来解决的世俗困境,是人在世间飘零时不可改变的残忍暴虐、毁灭消亡的倾向” 。很显然,科学资源、科技发展和物质力量的增长使人们的理性乐观主义精神日渐壮硕,挤占了传统神话、仪式、宗教、习俗等的空间 。但讽刺之处就在于,轻文明并未使人轻松,各种规约都日渐宽松,但生活本身却“重”了 。“轻”加剧了人们的脆弱和焦虑,人们最终的悲剧处境依然没有改善 。
- 汽油与柴油区别在哪 柴油和汽油的区别是什么
- 婴儿维生素D的作用和功效 婴儿维生素D的怎么补 如何合理补充维生素D
- 应的部首是啥 汉字应的部首是啥
- 有源滤波器 带通滤波器电路
- 铁线莲的根是什么样的 铁线莲就一个根可以发芽不
- 播种望高是啥意思 播种望高的含义
- angry的各种词性 angry的名词形式
- 木炭在氧气中燃烧的化学方程式 木炭在氧气中燃烧的现象
- 魍魉魑魅啥意思 魍魉魑魅的意思是啥
- 孕前冬季饮食注意事项 孕前冬季饮食注意事项 备孕的你要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