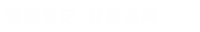《想象未来的玫瑰》,作者:费曼多·佩索阿,译者:杨铁军,版本:亚中文化中出版集团,2019年5月 。
诗歌翻译的第一标准是准确 。
新京报:诗歌的翻译一直是一个讨论不断的话题 。关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以及如何翻译有不同的观点 。在其他版本的名诗《烟店》中,最后一句中的“烟店老板”翻译成“烟店之神” 。为什么同一个词在中文里差别这么大?你认可什么翻译标准?
杨铁军:我看过的所有英文版本都是《烟草店主》或者《烟草店主》 。原葡萄牙语为Dono da Tabacaria,仅指烟草店主或烟草店主 。“烟店之神”一定是翻译错了 。我不知道那个翻译有什么依据 。
然而,我有一篇墨西哥作家帕兹的文章 。帕兹把烟店老板比作神,把烟店比作现代人的神庙 。这个解释挺有意思的,但是只有帕兹懂 。即使这种象征性的理解是正确的,我们也不能把“烟店老板”换成“烟店之神”,因为翻译就是翻译,不是解释,我们应该相读者的理解 。特别是翻译不要牵强附会,译者的理解,尤其是象征性的理解,要直接翻译成原文的意思 。更何况,Pass只说过烟店老板如神,从未直接说过“烟店之神” 。他发表的是评论,不是翻译,不能作为翻译的依据 。
关于翻译原则要说的东西太多了,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 。但是,简单来说,我认为翻译的第一标准是准确 。很多时候,只有准确性出来了,创意才谈得上 。准确性和创造性并不矛盾 。因为准确需要创意来呈现 。我见过太多的诗歌翻译家,他们觉得含糊不清,无法理解就好 。这样的译者是在编造东西,而不是创造东西 。我这里说的不是错漏 。偶尔,错误和遗漏是不可避免的 。我的意思是有些翻译,几乎每一句话,或者每一页都有两三处误解 。也许原文80%到90%的意思都被他翻出来了,但总是有点短,不管是外文还是中文的欠缺 。一本书都这样,你看不下去 。但是很多读者还是觉得不错的,因为这种翻译从80年代到现在培养了一批这样的读者,他们有着相同的审美期待,形成了恶性循环 。
诗人需要摆脱日常用语的束缚 。
新京报:作为诗人,你认为佩索阿的诗集有哪些值得你借鉴的地方?
杨铁军:我认为冈博斯的直率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 。我们很多作家都认为,所谓“诗在远方”,身边的人都在“相处” 。其实这种大众观念是对诗歌最大的误解 。冈博斯根本没有开始,他失去了开始的能力,并由此发展出一套反对“行动”的哲学 。他的世界可能有阁楼那么大,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厌倦 。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并不积极,甚至有点恶心 。就这样,颓废寒酸的主题被冈博斯用“直接”之刃劈开,让读者体验到最大的真实感和最粗糙的生活质感 。
这种“直接”和“即刻”看似简单,却包含了写作的全部奥秘,其实是最难的 。这往往需要几十年的工作,剥离复杂性和反复练习才能真正做到 。我们日常的话语,因为流行观念和历史观念的渗透,不由自主地将我们包裹在生活的洪流中 。一个诗人需要打破这些文字的遮蔽,达到理解的直接,才能真正站起来 。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。悲观的冈博斯有这样的勇气,所以他能做到真正的“直接” 。讽刺的是,冈博斯是一个不同的名字 。如果佩索阿没有这个与众不同的名字,他可能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。这说明勇气是一方面,也是开始,但好的文学虚构不是回避,而是加强 。
新京报:据说佩索阿留下的草稿有两万多 。目前中国读者应该认佩索阿是很小的一部分 。能否分享一些国外关于Pessoa的研究和发表的新内容?
杨铁军:应该说佩索阿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 。凯罗的全集已经由闵翻译成葡文,韩少功翻译的《奇遇录》是另一部重要作品,虽然内容不全 。程一身也有译本 。从目录上看,似乎包括了一些不同名称的诗歌和一些散文 。我翻译的这本书主要是冈博斯的短诗,包括《烟店》、《鸦片烟鬼》等长诗 。但不包括冈博斯的《海洋颂》、《胜利颂》以及向惠特曼致敬的长诗(黄在网上贴出了这些长诗的部分译文)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