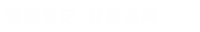这座楼是前线中的前线,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,所以它反而也是全书最自由、最有生命力的世界 。难怪苏军战线指挥部特地派来的政委(他们担心这个阵地的政治思想会走偏,所以命令一个政委冒着弹雨偷偷潜进指导),能在这里头发现危险的气息 。
曾在那座楼里和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并肩作战过的幸存士兵,则会事后慨叹:如果不认识这些人,生活还“能算是生活吗”?不要以为格罗斯曼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美化战争,挖苦和平 。不,没有几个作家会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无情 。
色彩这么丰富的“6—1号楼”竟然转眼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,没有临终遗言,也没有英雄面向镜头的最后笑容,十来二十个鲜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几行不到的文字里头 。这是格罗斯曼杀死他大部分角色的办法,说走就走 。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?那可全是行进中的漂亮生命呀?且再引一次琳达·格兰特(LindaGrant)的评语:“那是因为生命本来如此 。”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:“我所见的生命,都只是行过,无所谓完成 。”
和平也好,战争也好,在《生活与命运》里头皆是人类生存的严苛背景 。格罗斯曼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荒谬,托尔斯泰式的“正能量”几乎没有一点存在的机会 。
世界如此冷酷 。一个私底下对国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传人员,会在报纸评论上头指出,集体化政策之所以出现饥饿状况,是因为部分富农故意藏起粮食把自己饿死,好恶毒地抹黑国家 。
一个才瞎了双眼没多久的伤兵,退到后方医院,他在公共汽车站前请人帮忙登车,那些平时可能很懂得爱国爱军的平民百姓,却在车来的时刻自顾自地推挤拥上,不只不理会他,而且还把他撞倒在地上 。他“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 。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,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,他那一双瞎眼,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” 。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,站在那里又哭又叫 。一个瞎子,就这样被大家留在这片雪地 。
而伤兵医院里边,一个母亲终于找到了儿子,她对着尸体小声说话,怕他着凉还替他盖好被子 。所有人都对她的平静感到惊讶,却不知道这“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,又高兴,又拿舌头舔” 。
一个热心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在俄国住了一辈子,这时却被当做敌方间谍带走,向当局诬陷她的其实就是她的邻居,可能是为了趁机霸占她的屋子 。她的邻居不只不替她说话,而且还有意无意地用开水烫伤老奶奶留下来的猫,不久之后它也死了 。
一个一心向上的领导最喜欢关怀工人和农民的伙食,老在他们面前严词批评工厂厂长和地方干部,指责他们不真心为民服务 。他的言语通俗“接地气”,甚至偶尔带点粗话,老百姓没有不喜欢的 。可是一回到办公室,他却只谈数字和指标,要求下属削减群众的生活开支,提高工厂与农场的生产力 。
经过无数这样的细节之后,我还用得着说集中营里的惨况吗?就提一点好了,几个纳粹高官视察刚刚落成的毒气室,顺便在那四堵白墙之间举办晚宴 。桌布上是浪漫的烛火与盛着红酒的玻璃杯,他们对着美食举杯祝贺最后方案的成功,似乎后来死在里头的几百万人真是破坏世界卫生的害虫 。这是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世界,在苏式社会现实主义背景下练笔长成的格罗斯曼,冷冷地一字字刻写,犹如照相 。
电影《夜与雾》
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幸运,
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
不过,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,格罗斯曼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 。好比他战时笔记里的这一段:“当你坐下来想要写些关于战争的东西的时候,很奇怪,你总是会发现纸上的空间不够 。你写了坦克部队,写到了炮兵 。但忽然间,又会记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烧中的村庄上空飞舞 。”这多出来的一点点,不只为他的直白书写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诗意,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。
- 世界上十大最毒的毒蛇排名,你知道几个 世界十大最毒的毒蛇
- 盘点身价过亿的10位女明星:一个比一个有钱,你知道几个? 中国最富的十大女明星
- 中国最牛的50个道理,千金难买 中国之最50字短文
- 全球化妆品正品查询app,卖正品化妆品的app
- 庞统的*另有蹊跷其实这是他自导自演的戏
- 全国建立y库,道路的字母简称Y
- 全球最漂亮国旗,你知道几面?看看哪些国家上榜! 中国之最国旗图片高清
- 美国运载火箭技术短板暴露,中国用弹道导弹技术打卫星,太强悍了 火箭是中国之最吗
- 世界各国名人评价《道德经》 中国之最歌曲许子
- 中国最适合穷游的50个景点,花销不过千,你知道都是那里吗? 中国之最有哪些大数